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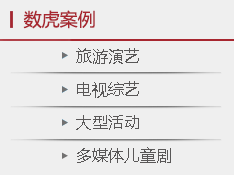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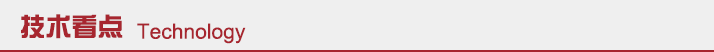
多年来,周正平同志的舞台灯光设计创作,是我一直较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在众多的当代中青年专家中,也是距离我的视野里最近的一位。我看过他搞的不少灯光设计的戏,无论在北京的舞台,还是在杭州的演出;无论是外省晋京的戏,还是在外地设计的剧目。林林总总,究竟有多少台,我一下子已很难列出来了。然而,总体的印象却是今我十分强烈和难以忘怀的。它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那浓酽的色调,那神幻的气氛,那营造的意境,和那倾诉的情愫,给舞台演出增光添彩的同时,也必须重新审视舞台灯光这门创造艺术了。无疑,周正平的灯光艺术,应该说已成了整体戏剧创造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了;进而换个角度来说,似乎其他表现手段也不可替代了。步入这种创造境界,是十分可贵的。因而,我将他冠以“佼佼者”,并不是过誉的褒扬。同时,也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欲望:试以文字来论述周正平的创造艺术,兼及当代我国舞台灯光的现状和艺术走向,甚属抛砖引玉,求教于同行大家。
(一)
要谈周正平的舞台灯光艺术,首先会将我们的目光投向他许许多多的创造过的舞台,也首先会在我们的脑子里,“过电影”一般地回想起当时观看的演出场面,这是很自然的事。舞台灯光的艺术创造,一是不能没有舞台,二是不能没有“时间”。换言之,它是时间和空间交融的艺术创造。所以,艺术家们将比喻成舞台上的“流动的彩笔”,正是贴切地描述了它的艺术个性或特性。
舞台灯光在当代的演出舞台上,已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个性化或特性化了。撩开周正平创造的舞台大幕,这个个性化或特性化的色彩,尤为显明的存在。象一股浓郁的醇香,朴面而来,让人陶醉。
我想概言之:舞台美。
周正平曾在湖北的《舞台美》中,以“彩色音乐”的艺术表现,作为自己灯光艺术的理想境界,从而创造“奇特的、活跃的艺术气氛”。我想,可以理解为对舞台美的一种追求。
创造舞台美,是一切舞台创造手段的终极目标。就拿舞台美术的表现手段来看,除了舞台的灯光之外,还包括舞台的布景,戏剧的人物造型(化妆、服装)等等,都有自己的美的追求和目标。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创造都能达到这个目标的,尤其是当它们作为整体舞台形象来表现的时候,能达到艺术的整体美,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舞台灯光通过种种的艺术和技术的手段,创造出令人们在观赏中感到愉悦、陶冶情致、乃至震撼的魅力,这个艺术效果,应该说,是达到了它的终极目标了。
90年代初期,一台古老的《西厢记》的戏剧,一出传统的、甚至已模式化的爱情故事,却在当今的舞台上,倾倒了许许多多的当代观众。这里,我认为是艺术家们创造了舞台艺术独特的现代的美感。我曾在评论此剧的一文中,写道:“舞台的现代美,也是当代观众的一种审美追求,这易于缩短观演之间的距离,易于亲近、认同,激发起观念审美情感。《西厢记》的这一个舞台上的创造,笼统地去重复‘反封建’的主题,已经不能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要了;同时,过分地去表现唧唧我我、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也会给人落入旧套。而必须进行引伸、拓展、深化、增大艺术表现的信息量,以期达到多视角、多方位、多元化的观赏满足。”(《小百花<西厢记>创作评论集》第13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这里,通过舞台美术包括舞台灯光的创造,舞台现代美得到了出色的呈现。它是一个重要的创造手段,营造了一种极致化的美的艺术氛围。所以,当代《西厢记》的舞台美,与其说是张扬了剧中张生和崔莺莺纯情的心灵美质,不如说是让每一个观剧人在舞台美的观赏中,获得一次纯美的心灵洗礼。
我始终认为,舞台美术家作为戏剧演出外部形象的创造者,主要的任务就是创造形式,创造可以直观的视觉形象。根据我的观剧经验,看完一台戏,能否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外在形式往往也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无论从不具独立性的个体、个例的美的形式的创造,还是包容内容的、获得共同认知和默契的形式美的体现,我认为它们始终是创造者的毕生寻找的生命线。周正平创造中的心灵脉络,也可以纳入这条线脉里去述说的。我想用美学家的语言来规范一下“形式”这个字眼。苏珊说:“形式”“在很多人看来,它包含的似乎是一种死的概念、一种空洞的外壳、一套无意义的公式、一种口惠;有时候它还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在行动、言语和工作中必须加以服从的规矩。”又说:“任何一种艺术品都是直接作用于知觉的个别形式,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形式,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形象一一它看上去似乎还具有某种生命的活力,或者说,它似乎具有人类的情感。”(〔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123页,124页)所以,我联系到周正平的灯光创造,尽管在一瞬间可以抹去舞台上的一切,却始终在创造戏剧演出的一种表现形式,包括所要表现的演出结构、演出色彩、演出气氛、演出节奏等。套用比较前卫的语汇,即创造演出的艺术符号。
周正平是在创造自己的艺术符号,只是用灯光的艺术手段。他的80年代的舞台创造态势,在我的印象中,应该说并不是处于自觉的状态,在所难免,还带着摹仿的印迹,去创造舞台的气氛,更多的是一种艺术的“描绘”。外部因素是他所参与灯光设计的剧目多是地方性的、传统的演出和传统的舞台格局,很难实施自己的艺术理想;主观因素也是存在的,对灯光作为一种创造形式的思考,还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虽然,从他撰写的文字中,已经初步意识到通过灯光手段,去开崛戏剧本体的内涵和舞台人物的心理空间等等,但还没有创造出自己相对突出的代表性作品。那末,进入90年代后,同样是创造,却已跃入了一个新的层面了。尤其是90年代初的从《西厢记》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作品,如《巧凤》、《宫墙柳》、《红楼梦》、《南唐遗事》、《琵琶记》、《寒情》、《荆钗记》等越剧,以及昆剧《少年游》、祁剧《走廊窄,走廊宽》、曲剧《茶馆》、话剧《生死场》等等。这些带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它的个性化和特性化的形式,可以用艺术符号来表述。周正平创造的灯光的艺术符号,才使舞台赢得了独特的生命力。
(二)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戈登?克雷早期的预言,他认为舞台灯光及其色彩均“含有暗示的力量以及各种材料潜在的表现能力。”是他第一个把灯光创造当作演出中的动力因素来运用的,从而促使戏剧在其美学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巴勃莱《爱德华?戈登?克雷》,转引自《论剧场艺术》第289页。)我审视周正平的创造,应当刮目相看的是他有着这方面的“潜力”。我认为由于他的近二十来在舞台上孜孜不倦地实践和创造,或者说以他作为一个当代灯光艺术家的代表的创造,已经改变或改造了舞台灯光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地位和艺术形象。灯光的传统功能,已经涵盖不了当今舞台的需要,在舞台整体创造中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自己创造的坐标。也就是说,现代灯光的表现力,已得到了进一步全新地开发(当然并未停止),灯光在舞台上的艺术形象需要重新的定位,重新的审视。周正平的灯光艺术,已经不“安份守纪”于传统的运作,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坐标。我似乎有一种感晤,创造舞台美的精灵,一直与他为伴;寻找和表现形式美的步伐,或者说寻找自己的艺术符号,也一直未曾停歇。
虽然议论艺术符号是一个美学中的命题,但同样与创造形式为首要任务的舞台美术及其舞台灯光,有着有机的关连,有着可以共同套用的美学尺标。“所谓艺术符号,也就是表现性形式,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符号,因为它并不传达某种超出了它自身的意义,因而我们不能说它包含着某种意义。它所包含的真正的东西是一种意味。”(同上,134页)舞台灯光在舞台上,不可能有舞台人物的那种有声的表演的语言(主要是台词),然而,它可以通过自己的造型手段,可以“无声胜有声”,创造出自己的艺术“语言”。要说“传达某种超出了它自身的意义”,产生“一种意味”。在舞台上,运用灯光的功能,是最为有效性的创造手段了。周正平在不同的剧目、不同的场所和不同的演出中,他驾驭的“表现性形式”,使灯光有了“意味”,有了生命的活力。
我想举两个例子。一是曲剧《茶馆》,二是话剧《生死场》。这两出舞台景的整体格局,并不是周正平以往经常遇到过的、轻车熟路的传统景观,但他在舞台创造中,颇有自己的意韵。
《茶馆》的景似乎更接近于话剧的写实性的布景。它在通常对称的室内景作了一些错位,让观众感受到舞台空调的调度更为丰富。这样,也极为有利于灯光对整个舞台空间的处理和气氛的渲染。
如灯光在茶馆空间层次切割上,有机地将背景、茶馆内、茶馆外统一在不变的空间中,使画面产生一种神秘感,增强了丰富的可视性。尤其是演出的尾声部分,残阳余辉中,一派凋落、苍凉、破败的灯光色调、层次和节奏的把握,首先为剧中的那个历史岁月、以王利发为代表的人物命运,哀婉地拨响了一曲时代的挽歌。这里的灯光语言,或者说它的表现性形式,作了积极的主动的参与,意蕴浓浓,使观赏者都会产生自己的种种联想。所以,由于灯光的出色“表演”,为整台演出亮丽地画上了最后的一笔,这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舞台绝唱。
《生死场》虽说是一个话剧舞台,却空灵如洗,一抹意写,不亚于传统的戏曲舞台。背景的“守旧”,厚实且朴实,是半浮雕的北方村落的隐约图像,它前面的几乎占满整个舞台空间的斜平台,什么物象皆无,无疑将要依靠演员的表演,来创造具体的人物生活环境了。宛如戏曲舞台上,让景在演员身上,“挥之能去,召之即来”般的空灵和自由。不过,舞台可以“空空”,但不能没有灯光的参与,而是需要灯光的“彩笔”去完成形式的创造。于是,我看到灯光的色调、明暗、方位等处理上,作了精心的设置。灯光没有过份去渲染自己,而始终把握一种凄然、压抑、低沉的情状,与戏的整体风格保持统一的步调,也与剧中的这群芸芸乡民的心态相印证。与其说灯光处理丰富和激活了一贯而终的、稳定的景的固定装置;不如说灯光是在张扬一种艺术的象征,一种外化为形象的时代的泣诉。最后,乡民们在血泊中醒悟,拿起大刀长矛,奋起抗日杀敌的一瞬间,舞台上突现的震撼人心场面,却却是由呆滞的背景装置和低调的灯光中完成的:半浮雕的“守旧”,中间突然蹦裂开了,呈现出一望无际的青纱帐,盎然一片,生机无限,乡民们终于觉醒,热血沸腾,打碎显愚昧落后的桎梏,奔向汹涌涛涛的抗日洪流中去!这个结尾,似乎没有其他的形式可以替代的了,赋予了诗一般的生命火花!
从这两个舞台的灯光处理,不难看到它“表演”份量,参与的份量,表现性形式的份量。表现性形式,已被美学家纳入“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学概念了。美学家贝克认为: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乃在于它们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他指出,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是由线条、色彩的某种特殊方式所组成的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这些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是审美地感人的形式。那末,在上述两出戏的舞台上,不正是通过线条、色彩及其“某种特殊方式”和及其“形式间的关系”等诸方面的创造,才有了“有意味的形式”,才有了艺术的火花。
(三)
“有意味的形式”是美学家对艺术作品的一种褒扬。套用到戏剧舞台上,也就是对舞台美术家创造的艺术肯定。灯光设计者在创造“有意味的形式”的阵地上,首当其冲,也是当之无愧的。
在周正平创造的艺术画廊里,忽隐忽显的“有意味的形式”创造是不胜枚举的。在我的印象里,越剧《西厢记》舞台的香火缭绕的几分神秘色彩的渲染;绍剧《大禹治水》中气势磅礴,展示了先民们与大自然搏斗的气派;《梨花情》、《白蛇传》、《西施断和缆》、《拜月记》等众多的越剧舞台上,诗中有情,画中有意,似诗如画,更令观众在观赏中产生了如痴似醉的艺术效果。周正平这些多姿多彩的创造,是寻找了自己的“艺术符号”,或达到了“有意味的形式”的美感。“有意味的形式,即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50页)这类表现形式,我想不同的文化背景,都会存在的。我想结合我们东方的、民族的艺术特性,结合已淀积了十分博大丰厚的我们文化传统,也就是说用我们的美学语言,归纳为两个字:意写。
意写,或者宽泛地说是写意,是我们艺术美学中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在我国传统的戏曲艺术舞台上,早已融汇贯通,并有了约定成俗的表现手法。戏剧家张庚说:“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是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征。这些特征,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剧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第4页)在这些特征中,我认为意写是它的主要创造手段,落实到舞台美术的创造上,传统舞台格局的程式化是与表演相呼应的,传统的“守旧”、一桌二椅等的舞台装置和装饰,以及表演者身上的服饰、面具等等,皆是“提纯”为约定成俗的、程式化的表现语言和手段了。在这一系列的表现语汇中,也是贯融意写的美学精神。周正平是从小在戏曲舞台上长大的,从他淌过的艺术足迹来看,他一起步就浸润在这个艺术的土壤里,耳染目濡,接受这种美学氛围的薰陶。所以,他的灯光创造中,自然而然将意写的艺术观念,水乳交融般地倾注在他创造的整体的全过程中,这是顺利成章的。
人们已经生动地比喻他是“灯光诗人”,正是说明他的意写的艺术观念和成功实践,成了他创造的主要特征了。
现代灯光之父阿披亚,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意识到灯光的超强的作用。他针对这支“流动的彩笔”说:“光之于空间,犹如声音之于时间,最善于表现其生命力。”(转引自吴光耀《西方演剧史论稿》第26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周正平在舞台灯光创作上的意写,着重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灯光心理色彩的意写,在是周正平搞的每一出舞台上,都能让人愉悦也感受到的。舞台色彩是极具有联想性、表情性、象征性。在演出的舞台上,它的不同色彩的冷暖、明暗,几乎都被注入了戏剧语言的影子,舞台人物的情感因素,包括引导观众愿意一起接受和享受这样那样的色彩诱惑。无论是表现一定舞台环境的客观色彩还是人物心理世界的主观色彩,都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煽情”功能。《寒情》舞台上色彩的反差、隐喻、渲染,已使戏剧思想得到了一定的升华的同时,也渐渐地打开了观众审美情感的闸门。“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马克思语)。所以,几乎所有的舞台艺术大师都不会忽视这个因素的。尤其在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舞台上,更被用来充当主要的创造手段。
周正平灯光色彩的运用中,还一点值得让人注意的,愈来愈走向单纯、淡泊、清雅,滤去了以往舞台上过分艳丽的成份。拿中国画中用墨的黑、白、灰来比喻,灯光色彩的黑、白、灰的运用,它所酿造的情调情境,并不亚于纷杂色调的铺张,而更显艺术的成熟。
阿披亚认为,舞台灯光有着“无可比拟的感情力量”,与东方艺术一样,一直透着强烈的精神性。灯光色彩运用在演出舞台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精神的体现。
(二)灯光空间结构上的意写,似乎在传统的舞台上,也已成了舞台画面造型的主要手段了。周正平绝大多数的数设计剧目是戏曲,而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戏曲的写意性有了较为共同的认识,布景设计也形成了相对空灵的格局。正是在这种创作“大气候”的背景下,周正平面对的舞台主要是中性的、虚空的、也是较为“简陋”的舞台,除了色彩外,舞台空间结构的调整、变化,舞台画面的多样和丰富,也得通过由灯光的手段来承担了。运用现代化的灯具,制造了光幕、光墙、光柱以及追光造型的多种画面效果,有的是局部的,有的是整体;有的是静态的,有的是流动的,顿使空灵的舞台、中性的舞台或中性的景观,变换得气象万千。绍剧《大禹治水》是比较空灵的舞台,但它要表现远古先民与水斗、与天地斗的壮阔变幻的场面,光依靠八卦形的转台,无论如何是营造不了种种治水的景象的。大面积的灯光调度、造型,彻底地改造了相对稳定的静置的景观。我认为是灯光有力量的、有生命的激活了演出多变的空间。
我在思考周正平驾驭灯光空间的诀窍时,似乎有这么一个规律:凡是空间关系比较成功的舞台,都是运用黑天幕(黑空背景)的舞台。扩而大之,宏观其他戏曲舞台上,也可以疏理这条创造的轨迹。
黑空,或者说虚空,无疑是中国传统绘画乃至表演艺术中,一种创造的表现原则,一种极致的美学境界。在舞台黑空的空间中,可以容纳更多的想象,更多的联想,调动和唤发起观众更丰富的创造力。“无声胜有声”,此刻在这里,则是“无形胜有形”了。因此,黑空的形式手段,正切合戏剧的假定性,也容易制造舞台的间离效果等等。这个美学话题,我暂不引伸开来议论,我针对周正平的灯光空间创造,由于他理解黑空的美学意义,于是作了充分的营造。他在空间上,大量的逆光效果,自然形成空间的距离感的;而在戏曲的传统表现美学上,正好找到了他们共同创造的交融点,使舞台有了符合观众审美习惯的意境。
因此,舞台灯光在制造空间中,已远胜于布景的表现力。即使在一个世纪前,也已经开始影响了阿披亚的设计思考。在他的艺术创造的序列表中,使他认为绘景(布景)不是最重要的,而应突出空间和灯光的造型作用。他强调,舞台设计已不再是通过绘景表达出来的静态画面,而是追随音乐和演员动作而不断由灯光加以塑造的活生生的舞台气氛。(参照吴光耀《20世纪西方舞台设计新貌》第7页)可见,灯光这支舞台的彩笔,已能定夺舞台空调的命运了。
我想再强调一下,灯光空间也存在着形式美,也有自己可操作的规律:整齐纯一;对称均衡;调和对比;比例相宜;节奏韵律;和谐等,都可以通过灯光空间及有关手段得到体现的。拿和谐而言,即多样统一,它是形式美的最高原则(也适合灯光创造中),它包容了其他内容,它体现出整个宇宙世间多样统一。这些规律,在舞台创造,包括在灯光创造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三)灯光也是时间的艺术,它与舞台空间一样,同样不能分割的。它的意写与表演一样,不能定格一种画面或一种动作上。所以,欣赏周正平的灯光创造,在拍摄下的、静态的画面上,是不可能充分领略其创造的奥秘的。与观赏一出戏、一位出色艺术家的表演一样,只能在现场的舞台上。就其意写而言,也只有在演出观赏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品味到它的意蕴。周正平的画册资料中,在同一台戏同一场场面,拍下了演出进程中灯光象电影镜头般的变化,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时间(当然包函空间)即演出流程灯光意写的魅力。近期,周正平的作品中,如话剧《生死场》、轻歌剧《玉鸟兵站》、大型歌舞剧《满都海琴斯》等舞台灯光,它的艺术独特的魅力,它的审美价值,它的震颤心灵的一刻,可能正在于流动的意写呵!
以上,我生硬地将这三个创造要素分割开来,只是为了述说的方便,而在实际舞台创作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种艺术的形式就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它们之间是融为一体,互补互生的,只是在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瞬间,某一个表现功能较为突出和张扬而已。就意写而言,我认为周正平谙熟戏曲写意的美学原则,他没有执拗地去背离,而是吸纳中去创造。因而,他的舞台,始终洋溢着美感,心灵的美感,始终为观众所喜闻乐见。
我仔细询问了一下周正平,与他合作过的导演主要是那一个类型和那一种层面?他的回答说那些导演都是合作比较多比较稳定的导演,而且都是属于较高层面的成熟的导演。这对周正平来说,无疑是十分幸运的,与导演有共同的创作观念,便会很顺利地找到共同能接受的“有意味的形式”,同步地进入创作的佳境。导演与灯光师的合作,必须都要有主动的创造精神,相互碰撞,相互进击中,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火花。
例如,周正平与导演杨小青的合作剧目,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记录、占据了他们合作的首位。我从得奖作品稍加统计,进入90年代以来,就有《陆游与唐琬》、《红丝错》、《西厢记》、《南唐遗事》、《大禹治水》、《西施断揽》、《荆钗记》等。这些演出剧目的成功率比较高,除了其他诸因素之外,可能灯光师与导演和谐、默契、长期的合作也是分不开的。导演杨小青可以在灯光设计者未在场的情况下,也可指挥一下灯光的事。从这一个小事,可以看到导演对灯光了解的程度了,这种相互密切的合作关系,已成了他们创造的成功之母也。
(三)灯光与当代科技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舞台美术是技术性、物质性很强的艺术创造,它是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的。当代舞台美术家斯沃博达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重视灯光,重视现代科技的运用。他的光幕、投影等技术手段的有机运用,使他的设计艺术一直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在舞台上愈来愈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舞台的艺术表现力因而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种运用当代科技,改观和发展未来舞台艺术面貌的走势,无疑还必将继续下去。
舞台灯光更是如此。不必回眸更远,20多年之前的灯光器材,而今看来是相当“原始”了。当时的光源功率不大,当时的灯具不能与现在用的电脑灯相比,当时的控制设备更无法与目前的数控调光台相提并论了。近20年来,新的灯光光源、新的灯具、新的设备等的大量运用和普及,不仅舞台整体的艺术表现力发生了突变,也大大地改变了灯光艺术的形象,好象张开了翅膀,能在舞台艺术的天空上翱翔起来了。因此说,舞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得益最大的就数灯光艺术和它的创造者。周正平正是一位这样的得益者,艺术创造的客观环境和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为他艺术才华的施展提供积极和有利的因素。
周正平是当代舞台科技的受益者,但这仅仅是外在的因素,也不能忽视内因的作用。周正平是较好地利用了这些因素,抓住了的机遇。他在利用当代舞台科技成果方面,是比较前卫的,使之在艺术创造的舞台上,折射出自己的光彩。眼下的舞台,当代科技的参与,它的艺术份量也变得越来越重。如近年一些投入大制作的舞台,主要是在显示舞台的“包装”,而“包装”的主要手段则是显示舞台科技的运用。虽然,这些高成本、大制作的舞台,在艺术创造上和经济回报上,获得成功者不多。但是在展示舞台科技的力量上,在转化为艺术形象的表现力上,却显示出自己的魅力和未来美好的前景。如前期演出的大型昆剧《牡丹亭》(上、中、下三本),由于运用大量的电脑投影灯具等现代灯具设备,使舞台上的声、光、色,世间、天府、阴曹,人、鬼、神,被衍释得淋漓尽致,张张扬扬。观众与其说是在观看杜丽娘的爱情悲剧,倒不如说是在欣赏当代舞台科技的一场“演示”。周正平在《孟姜女》、《寒情》、《大禹治水》、《玉鸟兵站》等好多的舞台上,也有过出色的“演示”,出色表现,达到了形式美的舞台佳境。
(五)
任何艺术家创造的成功因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两种因素的有机揉合,便奠定了成功的坚实基础。周正平所走过的艺术历程,从开始学步到今天潇洒、自如戏剧地在舞台上挥舞“流动的彩笔”,在客观环境上,正好赶上了舞台改革开放的一个新时期,一个艺术观念变革、纳新的新时期。他正是在这个极为有利的外在的机遇,加上主观的努力,勤奋的实践,摔打滚爬,在创造舞台上出类拔萃地获得了硕果。从他的身上,不妨可以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创作经验,至少是有益的体会,也包括一些有待提高的问题。我仍然拿他作为“靶子”,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首先,周正平时自己的艺术创造,有比较清醒的理性认识。他自己在不同的创作时期,进行过不同层面、视点的清理和总结,我认为对一位艺术实践者来说是相当必要的。如撰写的《光的心理空间造型》、《谈光色与音乐》、《体验自己平凡生活中的艺术经历》等文稿,就可以看成每一个时期创造的自我审视。他自己写的“创作理念”,我是将它看成他的创作宣言。我将它整段抄下:
“灯光艺术的处理,着重在揭示角色的思想、情感、心灵以创造精神意境,运用各种色彩,各种强弱的光,各种明暗对比,各种不同灯具的效用,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投入到戏剧情感的波涛之中与表演渗透溶化为一体。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人物心绪的变化而变化。成为人物心里的光、色反映,成为表演者的亲密伙伴,又为景物灌注了色彩、情感和生命,发挥灯火的潜在功能。”
这个“宣言”,虽然还可以写得再简短一些,但足已清晰地透视了他创作追求和理想。他对当代的灯光艺术,已从直观进入到哲理的思辩,已从静态的三维跃入动态的“四维”,有他自己的艺术定位。从而,使他的艺术品味,耐人咀嚼,充盈了诗的意蕴,这正是理性的思考、理论的滋润的结果。
(二)舞台灯光是实践的艺术。甚至也可以这么说,表演艺术是实践的艺术,舞台上其他艺术因素的创造,也是由“实践”这个舞台上得已兑现的。周正平已燃烧了20年的艺术生命,主要是扎根在“实践”的这块土地上,主要不是在课堂上而是踏在舞台上,尽管他至今还在学习。舞台灯光光恁纸面的勾勾画画,光停留在笔头的设计,是难以成气候的。这正是灯光艺术的特殊性。我所接触到的有成就的灯光艺术家,没有一个脱离舞台的,甚至始终与舞台为伍,从大幕打开到大幕闭上为止。道理似乎比较简单,灯光艺术